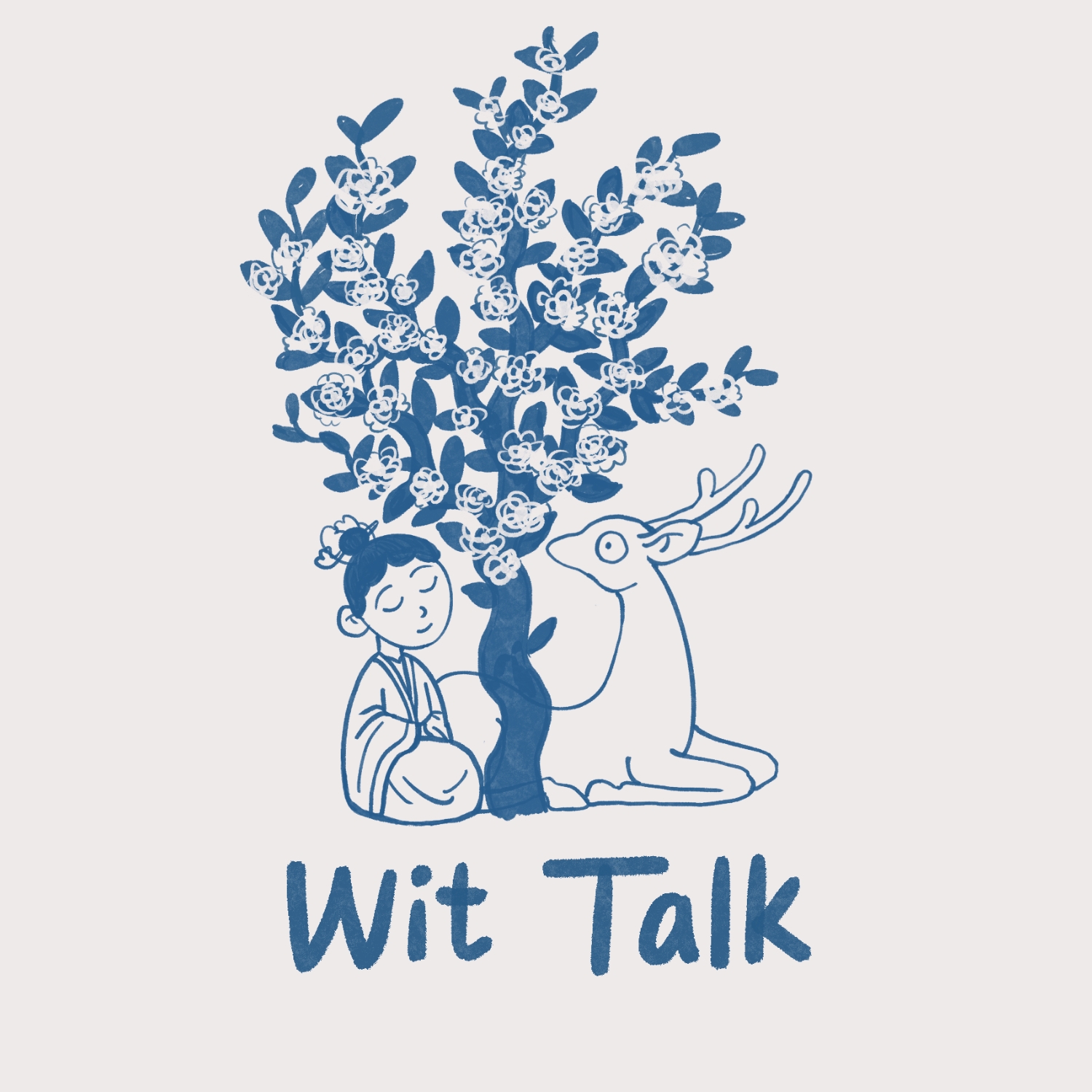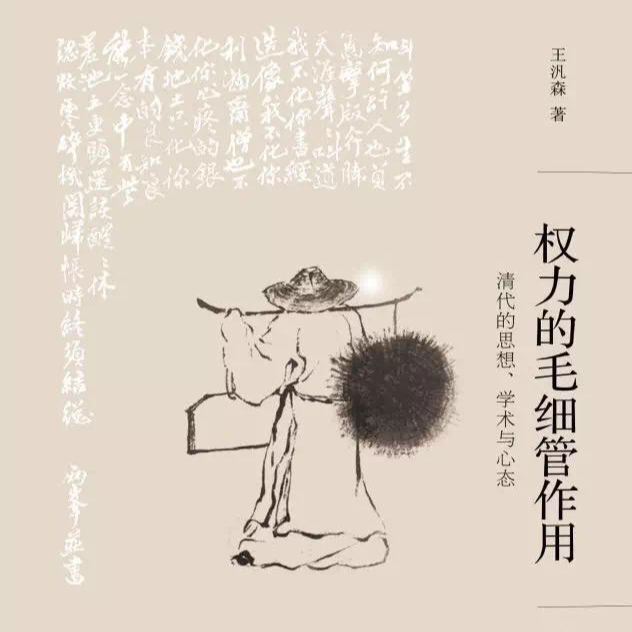
Shownotes Transcript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VTALK,我是主播刘晓树我想在这档节目中和你分享与哲学有关的一切本期呢我们想和听众分享另外一本非常优秀的思想史著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本书的第五章这一章关注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王阳明学说在明代的流行也使得一个观念流行开来那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种看似乐观的对人性的理解却反而造成了一批世代府高度的精神危机他们精神紧绷对自己任何一点沉溺和过恶都十分敏感而且深切自责
这种精神状态衍生出了很多帮助人改过的 SOP 形成了明摸清楚的一种十分具有特色的文化现象从他们的自白中我们发现想做更好的自己并在此过程中感到无尽的焦虑和迷茫这种心态原来从古至今都一直存在着
今天一起来聊天的嘉宾是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王璐老师以及东南大学的青年教师马天威老师他们的研究方向都是中国哲学我们频道的 logo 和片头也是天威友情绘制的所以如果想找到他可以在小红书和 B 站搜索聪明可爱马同学今天的节目马上开始《青年教师》
王范森的这个《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是王璐老师推荐的就是你为什么会推荐这个书给我们一起来读呢那我本人呢对于儒家内部的这样一个过恶问题呢是比较关注的因为西方其实有原罪论那在康德那里还有这个根本恶的问题其实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是有非常深入的缠发的然后其中涉及一些宗教的命题基督教也好还有这个佛教当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忏悔
反观的儒家在这一方面一直受人诟病的就是儒家对于人性的那种乐观主义的态度被很多人是认为一种近乎天真的道德乐观主义那比如说这个殷海光先生呀韦正通先生呀他们都对这个有
有这样一些批判那我们看到王凡森老师他这本书其实就是剖开了一个口子让我们看到在儒家这种所谓的道德乐观主义之下隐藏着非常深刻的一种道德的紧张还有对于人性内在昏暗面的这样一个警惕和克服对当下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这次我们跟听众来一起讨论的就是第五章的这个文章的名字叫明末清初的人谱与醒过会就是什么叫道德乐观主义我觉得王阳明好像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道德乐观主义的一个代表王凡森老师在这个书里面有提到过了
王阳明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说法就是满街都是圣人似乎透露了一种对人性的非常乐观的态度就高中的历史课本里面其实都会提到王阳明的良知学说那就这个良知学说为什么会导出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满街都是圣人就是在他看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良知那良知呢我们知道来源于孟子可以有两个方面的理解
一个方面说这个良呢就是先天本有自然而然比方说不学而能不略而知是不需要你后天去学习的不需要后天的反思就能够得到良就是善就是好所以这两个意思其实叠加在一起一方面它是你先天本有的然后同时呢这个东西是好的也就是说它不仅是每个人都具有而且每个人都能好
所以每个人就可以是圣人比如说一个人我去偷了隔壁王大妈家的一个苹果摘下来就吃特别好吃不是苹果又好吃贼味特别甜请问这个行为怎么能成为圣人这很不道德偷窃这个道理其实不复杂
比如说我口渴了我想吃一东西这能算错吗这不能算错我喜欢那个好味道能算错吗这个不能算错这只是一个我的非常中性的自然而然的这样一种动机这非常普遍但是你说错误在哪呢可能就是说我去偷这个行为本身可能出现了问题但从根子上说
从端序上说从根本上说这个没有错所以在他看来呢不存在本体意义上根本意义上的恶只是说善的过或者不及比方说我特别特别想吃然后我就不择手段那么我出问题了是这样的一种看法所以从根子上看他是这个闪随美人都能够成为圣人一提到这两只说法我就想起来
导师上课的时候经常举一个例子我每次到哪儿去面试或者给学生讲课我每次都必提这个例子这些理学家的这些讨论呢到底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能有多大的影响就你讨论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他说你现在看两个人在街边吵架然后他们就对骂就一个人说你小子没有良心然后另一个人就说你这人不讲天理那就是这后面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一个人需要有良心呢
然后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世界是需要有天理的呢所以这些讨论它今天已经沉淀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话语里面了好像变成我们的一种出场设置一样但实际上可能这些问题它沉淀在我们话语之前甚至从早期的时代这个开始就已经经过了这些思想家反复的讨论它一层一层的逐渐的下沉到了我们今天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底层逻辑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观念
和这个做法其实都有这些早期思想的这种根基在刚才呢马老师说那个偷苹果的这个案例啊忽然我就想到了奥古斯丁他忏悔录里面有很有名的一篇就是偷梨大概意思就是讲他小的时候呢去跑到邻居家去偷人家种的梨子那他偷完之后呢他也没有吃很多时候是用来把这个梨子扔掉
然后他通过这个事情就反省忏悔自己他说意识到他
他这个偷梨的这样一个得到的快乐并不在于这个梨子而在于偷就他本身作恶就有一种快乐所以这个快乐就让别人感到痛苦的同时他感到很快乐很刺激所以也就变成他发现人有这个天天生的向恶的这样一种倾向而变成他忏悔一个很重要的资源那这一点其实我们觉得是可以和儒家去做一个对照和对比的
对就这种挑战社会某种秩序的这种行为本身就特别刺激比如说大半夜现在估计外边就有飙车的哇你说飙车一方面他自己很爽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是那种突破限制我不要别人束缚我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爽但如果是杨明的话他会怎么说呢他说我想要快乐这个事本身没有什么错误甚至杨明有这样一句话叫乐是心之本体杨明后学泰州的王根乐学歌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
这种乐本身是从本体而来来自于这个良知他们这种想法下呢这个修行不应该是一种特别困苦特别充满着紧张的过程而是应该自然而然是一种乐的过程如果王阳明会认为
所谓恶是善的或过或不及就是我们本身自然的需求的一个扭曲的或者不正当的一个发挥所呈现的一个结果的话他本人的修行功夫里面他是怎么样教导他的弟子来为善去恶的呢首先是立志立必为圣人之志我觉得王耀明入门就是这一条进入到他这个
实践的螺旋我经常用螺旋做比喻就是一方面是良知一方面是接触物这两者之间是一个螺旋的运动过程你有良知不行你得发现出来然后你得在实践当中去践行这良知然后你践行之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活动去纯化自己的内在的这种道德意识
所以它就构成一个螺旋我光跟你这么说你肯定不会做因为你没有这开头这开头就在于两个字励志所以王耀明特别强调励志然后第二点就是你说他说时时念存天理去人欲反正就是经常要念存天理去人欲有的学生跟他说道德这个东西好像很自然不需要怎么修行王耀明特别反对这个观点
他认为初学者一定要做好为善取恶的格物功夫这格物就是把格解释为正就一定要有一个正的念头一定要把自己的恶东西给它格除掉所以这个过程在王耀明本人的思想当中是非常显著的
然后再往后可能就是有这种跟天理流行如何如何的这可能就是对于上根人或者说对于积雪已久的人以后达到的一种境界我觉得它大概是分这样三个层次
这个阳明学当中的这个过恶问题阳明学还是很重视这个改过和谦善的尤其是要靠不停的去改掉自己的过失得到自己恢复自己良知本体其实它也很一种内在的紧张的态度阳明好像把这种状态叫做如猫不属内心的精神状态是高度紧张的和刚才马老师讲的那种阳明学中
还另一面的那种道德之乐修德之乐这两种状态之间可能是有张力的我觉得比如说从宋代啊开始大家都会承认我作为一个学者我读书我就是要变成圣人承认这种可能性但是他是不是不像王阳明一样把他变成一个这么强烈的 slogan 嗯
因为
因为他们本身大部分出生于一个平民的阶层所以那个满街都是圣人就非常符合他们作为平民的这样一个自我身份的认同那这种把成圣的机会从过去的这样一个士大夫知识精英的群体然后下降到了一个平民的百姓其实是向平民敞开了这样一个成圣的一个通道
对在王阳明那里边橙色和金两的比喻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大圣人比如说尧舜这样的大圣人他们橙色又好他分量也很大但是比如说一个什么老百姓
也可以就是一个士大夫普普通通的他也可以通过自己这个为善取恶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变成圣人但是他可能在金两上付出这些大圣人但是成色上我们说 24K 纯金的都是一样的纯另外我补充一句就是那如猫捕鼠的这个比喻它来自于禅宗他比较强调的是
意识的团聚把整个意识都团在一点上就好像一种精神上的修行就是特别特别的专注于一件事之前是哪位理学家好像也是扬名后学的就是说什么是圣人然后有一个人马上被砍头了然后他说你看他现在心思的这种纯净就是一心想活这个状态就和圣人没有什么区别
真的我觉得这个很给我启发我之前一直在考虑的是他的那种内在紧张感没有注意到他这种寻中的这个状态其实这个很重要他来自于禅宗还有一个是叫母鸡抱卵其实一说的差不多就是总是在团聚在那个良知这个当中去但是你说紧张那多少也有点 196 页
他说可是上根者毕竟太少而中下根器者太多括号这是我说的然后在王阳明的学说里面可能上根者可以就是一下就发明自己的良知而中下根者需要勤勤恳恳的通过这个为善去恶的功夫最后来获得良知括号我的话结束了
这里面说到一些问题我觉得也蛮有意思他是讲这个王延明的后学里面产生了一些
非父名教所能击落的信徒我觉得王焕森的这一部分可能更多指的是就是王更这种就一批学生就特别自信就是从这个说法里获得了就极大的这个自信就觉得我就是圣人
王贯就比较典型嘛比如说他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就默作闭关静思有一天夜里他就梦见天塌了压在身上万人奔豪求救就看到日月星辰的那个位置全都错乱了然后我就用手就这个副手整支把日月星辰的位置全都整好了就那个时候他多大他 27 岁
整季苍生就龙傲天的感觉他出到江西去见王阳明的时候他也会穿着自己特制的那种仿古衣冠还有一些做法就是比如说他就是自治里一辆想象的孔子周游天下会坐那个车然后在车上就写上那个大横幅就在这个京师就是四处招摇最后被王阳明的弟子抓回去
他就还跪在那儿给王阳明认错被训斥了一顿所以他就是有这种拯救天下的自负我觉得他的一个理论的说法一方面是前面王老师说的他这个整个的台州学派的这种平民属性另一方面他从这个说法中会汲取的力量既然满街都是圣人然后我也有良知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圣人获得这样的一种信心
我觉得这个问题从古至今是有一点相像的比如说以前的古人会说我要成圣成贤然后但是他做圣人的这个过程中他就会有一种误区或者是危险会因为过度的自信然后就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自以妄为的行为
但是今天很多的鸡汤不也都是说要做自己吗最最流行的鸡汤就是你要做自己你要发现自己你剖析一下什么是自己呢然后这个自己和这种自以妄为和任性之间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一个情感冲动就是自己吗或者说我的欲念我的欲求都是自己吗就是面临的困境是相似的今天我们讲做自己好像总是它就是模模糊糊的一团
抛开这个问题里面其实我觉得里面还是有非常细密的这些更深层的维度需要去解决的就是对于古代这个成圣成贤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一样的对当我们说做自己的时候往往是想要摆脱某种外在的强力的对我们的束缚比如说我们免于贫困免于暴政
等等这些外在的对我们自由的这种束缚和挑战所谓的带引号的做自己就是你所谓的任意的时候我们被我们内部的一些欲望情绪这些不能够确定的东西控制其实和被外在的控制差不多这两者是一样的我们被另外一种内在的东西
控制了其实同样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自由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的对我们的这种束缚和压迫我们都应该去摆脱而摆脱的方法我们怎么区分真正意义上做自己还是肆意妄为我们做自己的同时还要在一起国家特别讲究实境性道德的完成一定要依赖于某种实境
那么这个实境的根据是什么呢这王耀明肯定说这就是良知就是我的良知会出现会判断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善的时刻同时他也会出现来审判或者说检查你的这个行为是不是符合了这个善就是他是两头鹵
我们的这样一个良知的这种道德的审判然后这样一个自由这样的问题那我忽然想到西方比如说像以色列柏林他们讨论的所谓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样的一些命题那什么情况下可以去追寻所谓的这样一个积极的自由什么样的情况下又这种追寻或者是对自由的追求又表现为一种拒绝和排斥的态度其实像他是
立基于一个西方对人性的看法和基础上那我觉得王凡森先生他的一个态度认为儒家这种道德乐观主义呢会延伸出两种完全极端的形式一种是充满乐观主义的态度对能够成圣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是极大肯定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在这种肯定的同时对于人性的这样一个堕落
人性的内在的昏暗面然后堕落为禽兽的这样一面有非常紧急和焦虑的一个态度就是不为圣人就为禽兽不为君子就为小人所以他对圣人和和这个禽兽君子和小人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非常敏感他要时时刻刻的改过非常严苛的去省察自己要拿着放大镜去看自己内心的所有的角落
所以我觉得这就使得儒家的这样一个醒过改过功夫日趋深入的同时呢又变得对内心的精神状态是高度敏感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比较自信的这个方面我们前面都已经讨论过了但是我们这次的主角还是后面的这一拨人第二百页呢他走向另外一个方向的一批人
就是因为阳明说人人胸中都有圣人固然可能是放荡不居的人自认为圣人但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呢他等于也把成圣规定为每个人责不可谢的义务因为每个人天生便是圣人所以一旦无法成圣便是自暴自弃也就是人天生就有绝对力量来控制自己所有的行为
故如果人在道德修养上软弱无力或变化无常那绝不是因为任何天生的缺陷而是自己努力不够完全无处可为过因而在道德修养上的紧张情绪也就非常强烈
因为对人缘聚的天性太过乐观所以会认为善才是正常的状态从而对现实生命中昏暗与陷溺的层面也愈为敏感甚至有通身都是罪过的感觉因此我们一方面在王门后学身上看到一些俗人自负为圣人同时也看到一些对人性近乎无知的乐观
却又对自身罪过极其深刻自觉与自责的例子他们常常挂在嘴上的口头传是如非其人即是禽兽括号我觉得这个观察的视角实在是非常的精彩
这段呢其实我觉得要涉及到就是儒家对治心理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开会会和一些社会学系的一些心理学专业的老师讨论他们都认为古代中国古代的心理治疗的案例是非常多的包括还有这个明代好多这样的一个日记也好啊或者是语录也好啊等等
他们其实就是把他这些视为儒家的一种内在的一个自我的省察然后对人性内在的这种复杂的一面昏暗的一面实际上有非常深刻的洞察那因为进入到这个近代以来呢随着这个反传统的这样一个运动呢很多的知识分子像殷海光先生 韦正通先生他们对儒家的一个明确的批评就是认为儒家对于人性这样一个最恶面的缺乏深刻的洞察
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去适应现代社会或者说和西方的所谓的现代文化进行一个对接和这个容赦
因此他们就认为儒家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化正是因为缺乏对罪恶的洞察所以没有办法在现代社会再继续的进行下去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他对儒家的这样一个本身的论述就会发现好像问题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这么简单那王范森先生在书中曾经引用到了美国华裔学者的五百亿老师的书他有一章专门讲在这个
十六世纪差不多这样一百年的时间内忽然出现大量这种自我忏悔的文本就是儒家士大夫文人有很多这样改过诵过或者是忏悔的这样一些的书写那不仅仅是有理学家还有文学家像袁忠道这样一些人
那么他们这种人有很多这样自我忏悔的这样文本出现呢在儒家传统中是非常反常和少见的因为儒家一直有一个所谓隐恶的传统就是不要过多谈论自己的恶或者是谈论这个他人的恶尤其是史记呀或者各种是传记的书写当中要为王者会为尊者会所以要有各种各样的隐恶把这些具体的不好的一些恶行恶人的行为要去省掉
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晚明开始出现了大量这种剖析自我忏悔自我的文本出现就有点像这个基督教忏悔文一样的东西开始不断的诉说书写自己哪里做错了
包括这个阳明后学很重要的人物王隆熙他也一次家中着火之后呢他就开始自诵说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其实这样的自我反省在儒家内部是很传统很正常的但是把自我反省变成文字保留下来这个现象是很独特的在晚明这个时期出现我可以认为他在那个时候变成一种风潮或者说一种现象级的做法吗
可能说这样一种醒过它变成一种思潮或者是有点夸大的因为思潮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是一个时代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影响我觉得悟宁说是一种动向或者是一种前流就像王冠森先生所谓的这样一个思想的前流和主流之间的一个不断的
其实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如果再往后延伸的话民国的时期呢报刊上有大量的那种忏悔文就忽然有人他就开始在报刊上去这个这个发表忏悔数落自己各种各样的过错
那其中玉达夫当然是最著名的了他的很多的成名作品中有很强烈的忏悔意识把自己内心的这样一种阴暗面然后就是向公众向大众去展开那其实这一点呢在传统的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儒家文化中是没有的只有佛教的这样一个忏悔才讲的是要当众当着僧众的面去忏悔
但是呢佛教中后来他忏悔文呢也并不主张要讲自己具体的罪业这一点也是隐去的所以呢这样一个要把这个罪恶当众抛白出来这样的传统儒家从来没有但是这个在晚明时期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动向是很独特的当然这个动向和宗教的影响也是有密切的关系对他形成了文字之后他得有读者他得有大量的读者吧
否则他刻那个板子都不够本的应该有很大量的读者需要这个东西他需要看别人的忏悔来实现自己的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真是挺有意思的这现象非常对于这样一个日记的这样一个修身方式呢西方有很多人在研究因为那个我们知道就是清教徒是吧西方的这个新教出来之后清教徒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这个
内部团契的一个方式就是写日记然后互相去传阅变成他们赎罪变成他们皈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凭借和证据那这时候就涉及到日记本身的一个悖论因为它日记自身是一种私人的书写但是它写出来之后又要被供来是阅读和传阅的所以它就有一个悖论在就是它为什么要写下来呢
他写下来其实是自己内心很私密的一些问题一些过错那他写下来还要给别人看在小团体内部甚至更广泛的范围内去流传所以他其实既有一种表演性在同时有一种张力在所以说呢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之前有篇文章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国古代的日记尤其是这种修身日记对于自身过错加以剖白加以书写的日记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我也感觉特别有意思我可能就是接续王汉芬先生那个思路我看他在这本书最开始也提到了这篇文章他想通过这两个包括第五章第六章这两篇文章去
像是势力一样来讲一下什么叫权力的毛细管效应我个人的语言来讲的话道德或者是共同体的成立就好像一个巨大的神话我们要不断的对这个神话去献祭
这种道德反省就好像是这个巨大的神话内化为这个反省者自己内部的然后他的这种反省行为也是像这样一种巨大的道德神话的一种献祭行为而当这种道德神话的中心是良知就是这个神好像是在内部的就要求着人要有一种内部的省察或者是技术的东西
来完成自己对这个神的献祭就不停地去做这个动作所以这个活动本身是我觉得是一种神话行为当然这个神话没有任何褒义或者贬义它只是一个客观的描述你觉得它带有一种宗教意味是吧我觉得它具有某种仪式性但是不见得是宗教性就像刚才田维说的它就像是这个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的一个在这个道德团体这个意义上的鲜活的一个例子吧
我们在展示这个例子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完全贬义的或者一个褒义的
人有这种自我反省或者改过千善或者他有一个所谓的良知的追求当然具体良知的规则就是如何判断他的善恶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是人有这样的一种追求它作为一种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是一件好事读书的时候上前老师课的时候他说这种事情它其实可以视为一种行为艺术就是自我的雕琢自我的雕刻其实是把自己的一生和自己的行为整个变成一个行为艺术品
我觉得他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就是带有美感的一种追求他确实是友好的一面同时他也有一种紧张的一面前面就说不做圣贤就是禽兽这种思路感一出来的时候当我觉得我全身都是罪恶全身都是病痛的时候在某些特定的人群里像我这样比较容易焦虑的性格里我就会瞬间焦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然后觉得自己这儿做不好那儿做不好他
他就会让我联想到比如说现在这个网络上呀千千万万为身材而极度焦虑的孩子他能控制饮食然后达到一个很完美的身材的时候这个事情完美很好他又会作为一个自律的标杆然后所有人都会赞美他对有一部分人来说他就会有这种现象今天我多吃了一顿或者说最近一周一过节我的这个
体重就崩掉了崩掉了之后呢随即让我整个人就感觉我自己就一无是处堕入一个深渊然后就开始陷入厌食症或者什么样就是他的这种标杆的力量他其实在有正面的这个作用的同时似乎也是会有一些这种负面的效应的可能性就王焕三老师他书里提到的这些人他们具体的这个状态我是对他们没有专门的研究所以
不敢说他们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也许人家是在一个比较自洽的状态里面这个严格对自身所以他就有形成一种神经的这样一个紧绷和过敏那我可以给你补充例子因为就我做古代日记的话我会发现有的人就会像你刚才说的例子一样比如黄纯耀明末的这样一个迅明的名臣黄纯耀他的
那个有两份日记其中就是有一份日记就是他在这个崇祯 17 年这个这个明王朝覆没那一年他写的在这个自杀之前呢你看到他能够每天的日记中就是自我反省每天对自己非常的不满
每天他日记中的内容是非常痛苦的当然这个痛苦肯定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他由于这种道德的紧张感而对自己导致的深刻不满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之前有国外学者就评价他是一个这个
就是内在是非常的神经质的高度敏感的一个人格他本身是近视嘛然后家庭条件也还可以但是呢他就是日记中却呈现出一种非常痛苦和挣扎的一个状态他不仅要禁止自己各种各样的欲望而且要把自己就是和当时的很多社交很多的这样一个社会的风俗隔离起来然后进行一个自我反省
他实际是比这个清教徒还要苛刻所以在这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精神压力是非常大的他不停的进入自己的梦境然后在那个梦境中他就有很多很难过的一个表现所以就造成了很焦虑的一个态度你阅读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他那种焦虑我补充一点就是关于那个身材焦虑我觉得这个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例子真的特别接近就是你比如说一个人追求健康他有问题吗他没有问题
我也希望自己健康每个人都喜欢健康看起来健美我自己看起来很开心别人看起来也很开心但是当这个健康变成了一种叙事变成一种带着社会的压力这种凝视我一定要健康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良知也是一样我有良知我从良知去做道德的事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但良知变成了一种
叙事甚至带着社会的那种权利这就是另外一个事情了有很多人就像刚刚王老师举的例子很极端控制自己的体重做出很多很多极端的事情这是我们在网上都可以看得到那他背后的这个道理就是说当健康当良知当这样一些美好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权利的
被鼓吹的范本它就变化了它内化了对吧把那套外在的规则完全的内化了它变成一种神话叙事对你就被裹挟着进入到这叙事里面我们可以说倒退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健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像现代的这样比如说男的要腹肌我们看明代的绘画猛将一定是胖子就是那种健硕的明代的绘画当中画的关羽一定是个特别胖的人
那个时候人认为那样才是鹦鹉是男子气概的表现然后给女生的标签就更多了然后女生就会把这个标准内化成她自己的一个她就认为我打扮我练成这样不是为了别人我就为了我自己开会就是我为了实现更好的我自己她那个自己其实已经是被塑造过的回到这个权力的毛细管效应这就是一种非常细微的
就是无远弗届的权利理学早期的一个奠基人像那个二成明代很多人的这个精神偶像成昊就是
就是他整个的这种气质所谓的修养的气质其实都是很洒脱的光风季月他是散发着一种松弛感的二成整体上都会讲你修养的时候不要太用力你用力就错了就是当你失去那松弛的时候就不对了他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他当然应该有紧张但不是那种刻意的用力的状态包括王阳明他到了晚期的时候他也是呈现了一种非常松弛一种浑然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它也是展示的儒家的这种精神修养或者自我雕琢的一种方向我们刻板印象当中的这种道学先生的紧张的状态我觉得不是整个的这种儒家的修养功夫的全部的面貌对就是良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它要有主动性我们举早起这个例子早起就是很爽
我们家旁边那个窗户就对着一个湖太阳出来的时候好棒啊但是这个是我主动感受到的我只能自律就是我觉得它很好我不能说别人也要这样做甚至我不能把它变成一种权利就是你一定要着急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什么特别依赖于这种社会的神话的这样的观念性的东西去指导我们的生活是因为很多人放弃了
对世界的感知我想说就是每个人当然不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每个人主动性他从自己的这种对世界真实的体会就我刚刚说的良知就是那个根那个牙那个苗那个端序每个人回到自己的意识最深处那个东西上然后去体会这个世界从自己出发做出一些判断然后才知道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不好所以良知的主动性
在我们现在生活可能是需要通过我们抛掉一些东西去获得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注意力的失确或者什么其实是一个社会性结构性的东西不是说一个人你得给人家好好注意注意哪那么容易啊
王凡森先生呢有一句话就是说人能否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其实我觉得他的很多研究都是可以找到这句话的影子那里面反映的答案呢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呢在我看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克服时代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影响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王阳明的满街都是圣人的这个观点引发的不同的两个面向也造成了一些道德的紧张对这个昏暗和沉溺极度敏感的人呢他们就会想要想尽各种办法去改过千善寻找一些更确定性的这个道德的准则后面就提到了明代的一个学者就明代哲学史那个书里面是说刘宗周说他是明代最后一位大儒
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对柔动中的一个定位就是改过千善赛道的王者我觉得他做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这个书中的 208 页这个地方王凡森先生他一开始就提出过改过从孔子那里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是中国思想史中不断出现的主题只不过阳明学的这样一个思想系统在道德修养上更倾向于改过一路因为阳明一再强调人天生就是一个纯精的圣人所以任何修养功夫只是去去毙去过然后要回返这个心的原初状态而不是在心上增添什么
但是在这个这个晚明王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改过是非常突出的那除了这个受到民间宗教啊公过阁的这样一个运动影响之外呢和阳明学自身也有密切关系
那么王帆曾先生他提到宫国阁运动其实就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现象就是我们知道由袁老凡老凡四训的这个作者袁皇由他来引领起的这样一个命由己造的这样一个结合佛教道教等等宗教形成的这样一个劝善运动
那么为什么会兴起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在儒家那一套非常高远的这样一个圣贤成圣成贤成君子这样一个理想不仅对于普通老百姓对于一般读书人来说呢也日渐丧失了吸引力就是说我从事这么辛苦的一个道德修养但是却不能保证一个现实的幸福不能保证自己的这样一个利益
不能保证自己有好的命运和结果这其实涉及到儒家的德福问题就是道德和幸福如何统一那我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圣人没有什么好处有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在今天也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要去帮助别人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普遍的现在也会有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在明代的时候这样一个三教合一的思潮当中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的突出以元皇为代表的这样一种宫国阁的思想主要就是说你做了多少善事这些善事会累积成一个数字然后这些数字就会在上天那里这样一个神圣殿堂当中被统计
那么然后呢再根据所做善事呢向你发放一个定额的福报比如说是吧这个人他没有儿子所以他做了多少件好事这样然后就会赐给他一个儿子那没有功名的话就做多少件好事就赐给他功名所以但是这样一个就道德的功利主义呢是受到儒家非常强烈的一个排斥的因为在儒家看来就是你
我们去修养德性啊德性修养成圣成贤不应该以任何功利的这样一个目标为这个目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就是拿这个道德去和利益去交换的这样一种人我是仔仔细细地读过那个《了凡四讯》的就是《了凡四讯》以及《宫国阁》引起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计算功计算过然后就是发放福报和发放惩罚的这个
影响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自己会感觉在《了凡思讯》的这个书里面它其实最后是有把这个消解掉的就是推崇佛教的一个书其实没有施舍的人也没有被施舍的对象然后中间施舍的行为这三个都是空的然后你这个施舍的行为不出于一个
求功利计算的心在这样的情景下你所得的这个功德是最大的如果你一旦计算那你这个功德就变小了就变成你格子上的一个这个小的数目他这个书里面其实两种录像是都有的所谓的功过格好像就是他有一个特殊的格子或者是一个本子类似的那种我也是通过那个看说他怎么算命命定了然后又通过功过格去改命
然后做好事这个功过格的这种记录的方式会流传开来因为它更容易普及你想那个三轮体空这种也很难你说一说行但是你怎么做呢它不容易做到一般的人更容易做到的还是我一天拿个本我把做的好事写下来坏事写下来它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可以操作的方式我的理解是这样
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公过格其实是变成一个可以自我评价的客观凭借的一个工具因为儒家好像从来也没有把这种自我的反省改过用这种程序化的仪式化的方式去进行
佛教其实有很多的忏悔仪式那基督教中也有忏悔仪式但是儒家在传统中很少有这样仪式化的这样一个程序所以我们看到在晚明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有各种各样客观的这样一个醒过改过的这样一个各种各样的团体也好日记也好它就变成一个客观记录的这种现象这宫国阁啊就和我们小时候那个打红花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
巨大无比那就是我画的没人名什么然后上面画一些什么小花我就给画画完之后然后老师往上印那个巨大无比贴一面墙然后做好事的就给个红印章做坏事的就是被老师批评了就印一黑印章刚开始大伙还是有一点警示作用
大家都怕被黑印章但是为什么有警示作用一方面就是自己觉得脸上不好看最重要的是家长会家长会看到后来我们可能也长大了就无所谓了就放飞自我了但是我觉得和宫歌歌有点像就是它填不填是一回事但有这么个表它还是会有点震慑力
他究竟通过什么来判断善还是恶呢就是他还是要通过一些大家普遍认可的这个供需良俗一些习俗上的东西去判断善还是恶真正意义上的伦理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东西实现的田维书的这个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个人也会觉得就是他律的这些规则
我不完全否定它的作用比如说所谓的一时一地的这个所谓的公序良俗或者说法律规定我个人会觉得如果它在这个一时一地还是一个适用的状态就是根据它去进行反省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又回到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从我的完全从我自新的一个
感知出发然后去发展出一套比如说属于我自己的具有我个人差异性的这个道德律当然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就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或者说这种感知力当没有达到的时候他采用一些就是他律的手段这就是钱德宏和王隆熙的那个天权正道之争嘛就他采用一些他律的手段来去规范和约束在最后再取消掉这些束缚
就有点像今天闲着没事放在家刷刷手机我觉得我 B 站没刷太久啊但是如果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屏幕使用时间记录然后我一打开我就发现哇当我看到确实在这个软件上挖掉了一些我不愿意花的时间的时候那我可以发挥一些主动性看看后面是不是能把这个时间降低而且当它变成一个比如说我想要去记录的时候
它就好像是冥冥当中旁边有一个监督者在监督我的行为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长期的使用一些时间记录的软件来记录我做每一件事情花的事情我可能因为为了要获得一个比较完美的时间表而去下意识的去规范我的这个一些的行为天威说的这个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个人也会觉得就是他律的这些规则
我不完全否定它的作用比如说所谓的一时一地的这个所谓的公序良俗或者说法律规定我个人会觉得如果它在这个一时一地还是一个适用的状态就是根据它去进行反省不一定是一个坏事我也有这个体会我们觉得精神放松的时候会画出更好的画
但我的体会是不是这样的你必须得大量的话大量的失败然后把自己限定在这个世界里不停的滑然后才能画出一幅自己满意的话这才能进入到那个状态里边去我完全赞同这个我想说的是
伦理和刚刚那个区别是在于伦理是要和人打交道和人打交道我就没有办法用一个表格因为他也有他的良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都是意义的源泉都在向外涌出意义那我怎么能和一个他者就是一个他人去打交道这个东西才能构成伦理我怎么能够和一个人好好的相处是我首先要尊重他是一个人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王老师来给我们补充一下因为你是研究过的明代中晚期的这些儒家从佛道教里面学习他们也发明出了一些所谓的宫国阁其实我们是吴政老师或者是王凡森老师把它叫做儒门宫国阁我个人更倾向于用修身日记来代替这个现象修身日记在儒家起源是非常早的
就是宋代至少是在宋代已经有了但是呢并不普及和不流行因为刚才就像前面所说一样就是对于自我过恶的揭示过错的揭示剖析自我书写这种阴暗面的这种传统的和儒家这种隐恶的传统是相违背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到了晚明的时候呢一个明显趋势就是用来醒过的记录过错的这样一个修身日记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很多学者认为它和宗教的这样一个刺激有关但我认为应该从这个儒家传统自身去找到一个线索
就是说宗教可能是一个外源就是外在的一个刺激来源但是呢就是更多的问题是在于儒家原来那一套省察改过的方法没有办法再去解决心灵焦虑的问题或者道德堕落的问题等等这些东西它就儒家传统那些的解决方案到了晚明的这个时候它开始暴露出种种弊端了
所以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了所以这时候才会出现这么多的一种自我书写或者是自我省察的一个客观的程序也好而且儒家的修身日记特别强调就是说他和宗教那些劝善书公过格一样不同的地方在于就是他不要求记善那我们看到公过格就是要求我记录做多少件善事我把它记下来这样我才能够得到多少福报
儒家这个功过格是不一样的他们特别要强调要记过就是以记过为目标比如说刘宗周还有陆士怡就是明末清初宗周地区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他们也在强调就是一定要记过而不是要去记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好事那这就和宗教呢这个道德功利主义形成一个截然相反的态度
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在强调不要讲自己做了多少好事而要讲自己改正了多少过错不断减掉自己这个良知之心上面的这样一个遮蔽不断地通过改过千善然后变成一个圣人或者更好的人
刘宗周的人谱当中他就会罗列很多的过比如说微过 隐过 大过 从过等等各种各样的过错里面就记录各种各样的条目比如说是不是对家里人不好和朋友交往的时候你有没有诚实守信或者你在外头处事有没有符合礼仪等等
刚才马老师讲的就是人际关系中对方的一个主体性问题就是说他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记过格中的他并不考虑一个主体性他只考虑的是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伦理秩序当中的位置比如你是儿子你就要做到怎么样的孝敬你是臣子的话你要做到怎么样的去中军
所以说你是朋友的话你有没有去尊重你的朋友有没有符合礼仪所以是完全根据这个人在伦理等级上面的位置去判定你做什么对比一下魏晋时期我们看到那些魏晋的那些玄学家比如说像阮吉是吧他就是非常的轻松比如他可以喝醉酒就躺在女性旁边但是他内心没有这种我们今天看来是这种肮脏的东西没有所以他没有这样一个紧张感
那在理学家或道学家的群体中呢就社会评价的标准越来越严格所以他们对自我省察的这样一个视角也越来越严密有点像我们一些网上的氛围一样就是容错率不管是对于自己还是别人的容错率也是越来越低的就是变得越来越严格我就说现在 B 站很多节目
网络上很多视频都是要叠各种把护叠各种假说我这个既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个然后你千万不要跟我干啊怎么怎么样对就是你说的越来越严格说回刘宗周他对自己的这些道德要求我还是有点没太弄明白就是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知道宫过阁的方式他是有一个表格
那我做了研究之后就发现它们的形式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有的形式呢很零散就是说它什么都不标比如说像明初的理学家吴宇碧啊他的日记就什么都不标他就是在前面每一年的前面标注一下年份然后呢
在其中他就可能每天都会写一点今天的状态怎么样今天做了哪些事比如说他今天又跟谁发脾气了骂人了他就写下来第二天他可能看到了一片很美的自然风景他感觉很好他又写下来这种是一种很松散的形式那么还有一种比较严格的形式这种形式他就会严格按照我们今天所看到日记一样他标注年月月
日然后还有的甚至会在日记上面打一些表格格物没有诚意没有正心没有修身没有这些方面他给自己打格然后每天去在上面打这个圆圈或者差比如说像杨明后学罗鲁芳呢他的日记就是他就会在这个日记上面打格然后
甚至要检查自己每天的梦境清不清他的心平不平静等等他一天下来之后都要在这几个选项上去打隔还有像陆氏仪也是陆氏仪的日记就分为什么成正格制这样的一些几条然后每一条下面他就会检查自己一天下来包括他的好朋友陈胡等等也是的像这个他那个小学入门书一样把每一天都分成一格一格的然后按照那些标准去
这个判断自己比如说就是你有没有孝顺父母呀有没有好好去读书啊每天都要对着这个表格自我检查如果有的话如果做对了做到了就打个勾啊没有做到就打个插会儿圈那么到了一个月的月底或者中旬下来一检查就知道我这个月表现怎么样然后再进行一个自我的判断我感觉听起来有点像一个明代的手杖体系嗯
对对对有这个意思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做各种手账然后写各种打卡做各种记录什么心情记录啊学习状态记录健康画歌诗各样的那个形式和记录的表格而且他们那里面的就是除了这种日记中除了这样一个个人道德情况呢也会记录一些别的包括一些日常的交往啊或者读书啊或者其他乱七八糟事情都会记录
但有的日记会格外凸显自己这个心的情况我还有一个问题根据你看到的这些日记或者这些手帐吧
肯定会记录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善恶的标准他以客观的居多还是主观的居多呢因为我们知道宗教里面的那种功过格因为他一般是面向这个普通大众的客观的那些条目可能会更多一些我拿到一份印刷好的我就填这就完了
那么这样一个日记中记录的这样一些过错呢其实也是分层级的比如以刘宗周的人谱为例呢他在里面列了什么显过呀微过呀等等之类的那么比如说这项从过大过等等都是表现在外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的举止动作有没有符合礼仪啊等等有没有说脏话甚至有没有可能这个走路不合规矩这些都是外在的那么还有一个叫隐过那么就是在他意念当中有没有起思
刘宗周之所以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这个赛道上的一个王者因为我读刘宗周的这一些语录啊介绍刘宗周的书籍因为王亚明他就会讲良知就像一个卫士一样然后站在门口那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这个卫士就检查一下你是善还是恶然后你是恶的话就不让你出去很多人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刘宗周批判的也是这样的一种观念刘宗周就会觉得当你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我这个卫士再去检查已经晚了
你就在那个就是将出未出在那个意念最萌动的它就有一个很经典的比喻叫罗盘吧罗盘跟个勺子它总是有一个指向某一个方向的潜在的动力那个潜在的动力才是你这个人行为的最根本的一个动因我觉得这个其实从精神治疗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好像已经从表意识走入潜意识的一种感觉对对对而且这个是很早的时期比如说今天我们分析很多问题你讲无能狂怒你表面上是愤怒然后你底层的潜意识可能是对自己无能的一种无奈内心的这种潜意识会驱动人做出很多表面的行动只通过对自己的反省和剖白能走到这么深我觉得是一个很难想象的
那其实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是有非常多的心理资料的就是在这些语录啊日记啊各种各样的文献记录中有很多的心理学的史料在里面他们这些儒家呢对自己内心呢或者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呢对自己内心那些非常微妙的动态的一个捕捉然后把他们记录下来记录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客观的呈现的过程中因为在书写过程里
他们要反过来再去回味自己的心理状态然后去尽可能精准的捕获它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内心其实就会分裂成很多个角度一个是当时的这样一个反应一个是一个观察者还有一个记录者所以就分裂成了很多一个人格或者很多一个角度
赵王范三老师的这个思路来说呢即便到这么细密的地步他恐怕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所坚持的这个标准到底是不是一个对的或者说我今天这个反省到底是不是一个符合圣人之道的在他们的叙述里面就应该是是不是符合圣人之道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跟今天的什么有点像很多人很沉迷于在小红书上判案就我今天和男朋友女朋友吵架了把聊天记录截成几张图然后发在小红书上或者我今天跟我父母产生什么矛盾了我的心路历程是如何如何然后小红书书友们大家给我判断一下是我太敏感了吗就是王河森老师书里他说到因为他无法自己判断我的这个记录到底是不是一个符合圣人之道所以它导致了会聚集一群人
导致这个醒过会的出现然后我来剖析我自己然后大家来互相的这个评判剖析觉得这个例子非常贴切他好像说自然而然会出现的一个事情他提出的一点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在 217 页他说刘宗周所说的暗中之名就是指私欲很技巧改一个手势让良知被骗而使得这些私欲与习心能通过良知的检查
他就会提到人在自省的过程当中常会遇到的一个自欺欺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当你听到一个人他在向你倾诉他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听到一番他的剖白
你往往觉得他都是理直气壮或者是义正词严很多人会把自己的一些思念思欲包装成一个正义的样子而且呢这个东西呢和他的学历和甚至他的理性能力都没有关系是的没关系他有可能理性能力越发达他包装的越精巧
因为我看到的很多就是在小红书醒过会里面求大家评判的人的自白里面就很多这种文过是非大家就会在评论里面就是对他讥讽本来他想让别人替他说话是吧结果就迎来大家的审判我猜想在明末的这个醒过会里面可能会大量会存在类似这样的场景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晚明王学有一个人叫孟化礼啊他后学那他有一篇文章好像就叫三子醒过不序他们这样一个地区呢组织这样一个醒过会那其中就有几个晚辈嘛这几个人就把他们记的这个日记呢就拿给他看啊拿给他看这日记其实就共同在上面记录自己一些过错那么
那么他看了之后他就写到啊他说你们记录的这个东西可能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而真实的一些内在的深刻的过错你们并没有记录或者自己没有深刻的认识到所以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醒过的本子也好啊
反而会变成一个文过是非的一个方式修饰自己过错一个方式所以最后呢梦话里就说要求他们要深刻反省自己内在的内心的这样一个过恶内心这样一个昏暗面而不是夸夸其谈的写一些表面的错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日记的本身可能存在的弊端也是有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在里面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于还是刚刚我说的这个区别就是人和人之间这个知非对错是特别难但是我觉得这里哲学问题就是伦理是不是一种能够诉诸理性公开讨论的事情是不是大多数人说这样对就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取决于知识的形式就知识的形态就如果这种是一种
圣人性的知识就得靠这种良知去判断如果它是一种类似于民主式的知识形态那么是可以通过理性的公开讨论就是康德就是干这个就是康德拼命的要搞一个就是能够通过时间理性来说明的这样一种道德但中国好像很难就是至少在宋明理学的这样一种圣人式的知识性
是很难实现的就是大家都说你不对那就真的不对吗对吧他肯定说只有圣人说不对才能不对那圣人在哪呢圣人在你心里
我只有通过成为圣人这个就闭环了其实还是上位者或者是掌握权力的人才能够判断善恶和失败所以又回到了王老师这出的题目就是权力的毛血还要请王老师再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他们具体是用什么形式我们今天当然我们可以拉个微信群或者是大家约个时间咖啡馆坐着喝喝茶
或者是小红书发个帖子来征求大家意见那就是在明代的时候要怎么那么关于这个晚明的醒过会的研究呢我并不多因为我主要是研究一些文本但是像王帆森老师书中其实有专门的介绍那根据他的介绍呢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是有各种各样的醒过会的形式一样
他们也是像日记一样有的是那种松散的或者是严密的组织当时还有很多相约嘛就地方这个乡村社会他们会组成这种相约然后定期的把乡村父老都召集到一起去宣讲一些圣谕啊讲一些善恶果报的故事那在其中呢会设两个这样一个本子一个本子就是改过把这些参会的这些父老乡亲他们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过失呀他们自己记录上去还有一个是谦善就上面有一些他们有什么好的事情也记录上去变成两个形式但是呢在读书人内部呢他们还有就是这种醒过会呢其实往往伴随着一个讲学会这种讲学就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这样一个小型的巡回演唱会之类的这样一个形式歌友会这些形式
那么在这种小的群体内部讲学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互相拿出自己记录的这样一个醒过步或者修身日记然后互相的去批评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他们就会在这个时候提到这个对方的最近的表现如何有没有改正还有一种就是更小的团体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黄纯耀他们这样一个团体就专门是为改过而成立的
这种团体其实也并不多还有一种像是静坐比如说在这个明末的时候无锡就有一个所谓的静坐会他们就是先通先像采用高盘龙那一套静坐法先静坐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再互相的然后拿出他们这个改过的这样一些记录来然后互相的醒过互相的检讨所以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醒过会很少是一个单独的或纯粹独立存在一个组织经常结合一些讲学呀或者是相约呀或者静坐呀其他一些形式呢一起去进行的你会怎么来去评价这些
醒过会的作用呢做学术研究的话肯定是尽量保持客观中立的不带一些过度的个人价值评判在里面但是就效果来说呢我觉得它是起到一个首先是自我认同自我标榜的一个效果首先呢它自我认同是圣学嘛它要做圣人所以它要通过这种小的这种团体呢强化一个自我认同感另外一个就集体的凝聚力就是他们认为世道再昏沉再昏暗
还是有我们这样一群人在承担着这样一个道统承担着这样一个学术思想还有社会文化一个复兴的重任它增加了这样一个凝聚力比如说清初的它这个静坐会就是这样那当时的静坐会主要是一群在地方教这个私塾的这样一群小的地方的读书人
通过这个呢他来坚定自己的道心增强他们自己这个集体的凝聚力道学传承在他们自己这一小群人身上所以呢就再通过他们的再向基层社会去扩散
但其实我认为这个现象虽然很独特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它扩大化因为它的影响反而我觉得它起到一个限制儒家社会化的一个局限性的作用因为它的那个就是儒家圣俗之别它把它强化了
阻碍了这个这种儒家思想继续向基层社会去扩展阻碍了儒家继续去社会化大众化和平民化的一个障碍变成一群知识分子或者知识精英他自我标榜的一个东西一个标签一样
他们这个醒过会的小团体是不允许其他成分的人参加的吗那他们这样一些醒过会的小团体呢也是允许其他人参加的但是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一个道德要求的他们特别反感一些这个
比如说经商的人商人或者是一些虚名孤民钓鱼之徒啊这些人他们不要啊就很强烈的这样一个圣俗之别那这种圣俗之别呢就阻碍了儒家一个社会性格的扩散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分化啊四川大学的张璇老师有一本书就叫做从此殊途啊就是说从这个时候把明末清初开始儒家
和这个平民的这种社会文化之间就开始分道扬镳走差了走远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道学先生的这种刻板印象就是那种很古朴的一板一眼的然后有很多教条规则的鲁迅批判的那种孔义己式的那种形象这个所谓的这个醒国会或者是当时的这样一些
运动它是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之一吗那我们今天说的儒家这样一个道学先生的这种刻板印象啊这样是由醒过会来造成的吗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跟儒家一直以来的这样一个道德理想主义本身就是要强调君子和小人圣人和这个凡夫俗子之间的区别但是小人其实并不是说所谓的坏人他可能一开始只是一个社会身份上的区别
但是呢这种就带有一种强烈的身份的标识最后变成一种人格道德品格的一个标识做出一个区分儒家本身他就内在有这样一个区分有强烈的一种精英的意识所以是他要标榜就不管是他穿长衫也好还是他言谈举止也好还是他内在的道德修养也好
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划分那么刚才就像我们说这样一个醒过会也好他要标榜自己这样一个身份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而阳明学派中的出现的泰州学派这样
那种平民化平民主义的风格其实反而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他打破了儒家传统的这样一个阶层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平民主义的意识所以这个反而是在儒家中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刚开始儒家师大夫是希望
获得君主的赞同然后向下去做然后到明代的中后期可能真的发现了一个转向就是您说的尤其是太昼是最明显的希望能够通过绝民去行道从德军行道到绝民行道的一个转变
他究竟真的到绝民了吗还是绝民变成了他们的某种标签变成反而是一种自我标榜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吸引我的一个点不管是绝民行道也好德军行道也好他其实本身他都有一种强烈的一种承担道统承担这样一个天道的这样一个自觉意识或者是一种精英的一种文化优越感
所以不管是绝民也好还是德军也好他都要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去规范这些老百姓或者去规范君主而绝对不是说跟老百姓他是站在一个层次的所以我们说他清明也好清明也好其实呢都是要作为明的一个引导者而并不是把自己本身作为明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说这我就想到王阳明传奇录第一条
是第一条吧就说这个亲民的这个问题第一条就是亲民朱子说亲民就是新民让老百姓焕然一新王永明说不是的亲民就是亲民亲之即人之人爱去体会老百姓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识人嘛编转串起路把它放到前面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小宇宙的频道呢突破了 7000 粉丝为了感谢大家呢我们会在评论区挑选两位粉丝朋友各送出一本王凡森老师的这部经典的作品《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也期待在评论区听到你们的声音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