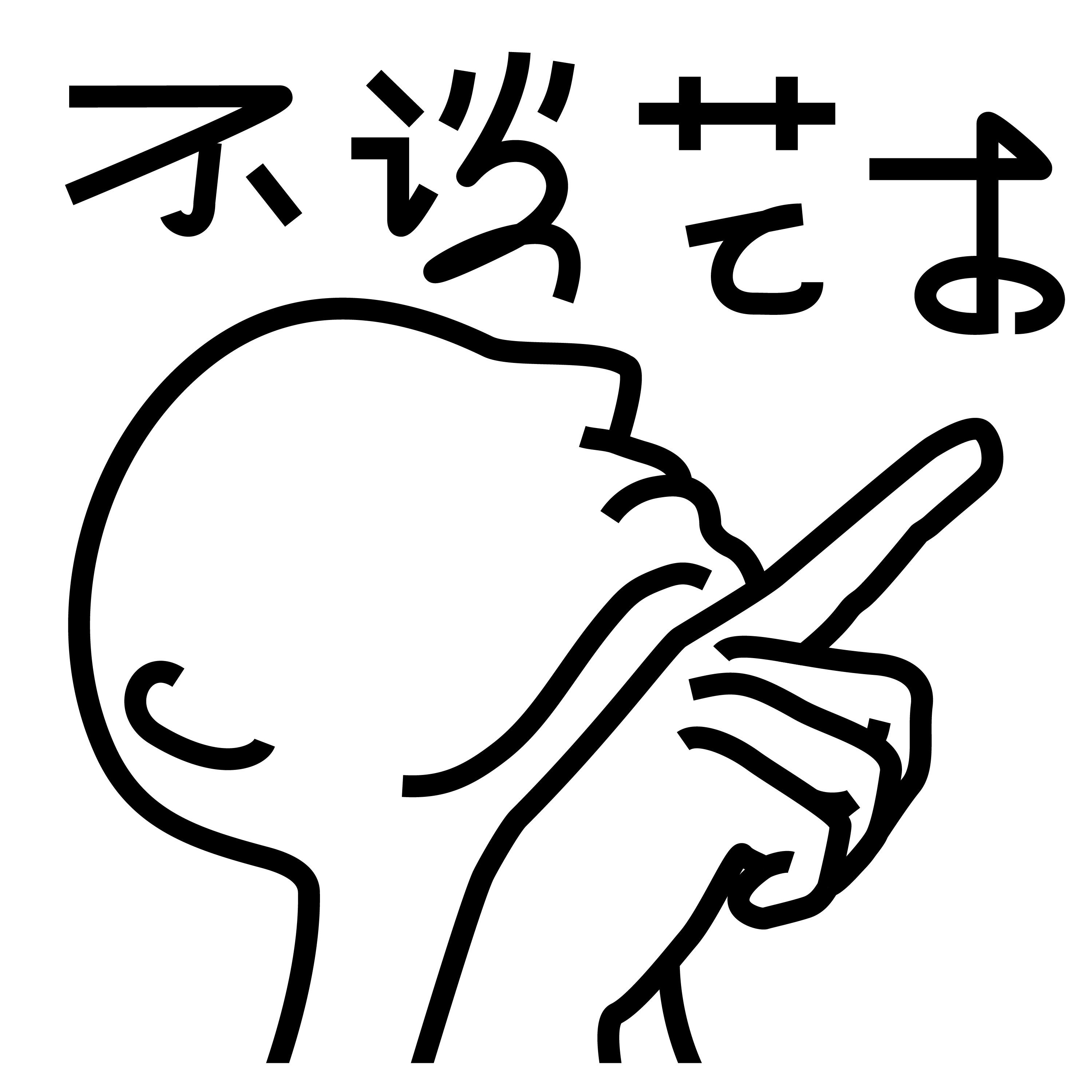
房
房方
苗
苗炜
房方:疫情期间,人们主要通过聊天来消磨时间,而疫情反而促进了她的写作,她认为写作状态会在疫情结束后好转。她还谈到了作家可能会有一个创作的“反作用力”,以及人们会通过阅读来逃避现实,专注于当下能让人暂时忘却焦虑。她认为对特定事物感兴趣可能是因为逃避现实的策略,并认为建筑和文字都很重要,但常识难以形成共识。疫情改变了她的写作节奏,让她适应了在家写作,但她认为不能外出玩耍让她感到别扭,这主要受心情影响。她还预测未来信息减少,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划定自己的小圈子,减少与大世界的联系,并认为人们减少社交,也可能导致对他人同理心的减少。在特殊时期,人们会通过一些简单的活动来寻找慰藉,例如跑步和听播客。她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的商业环境会很糟糕,但她选择屏蔽负面经济信息。她的盈利模式与电视剧产业无关,她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并对鸡蛋这种廉价的蛋白质来源印象深刻。她认为物价相对稳定,一个鸡蛋大约一块钱,但她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很高,并不在意鸡蛋的价格。她会通过阅读历史事件来进行心理建设,并认为文化需求增加是因为人们实际生活体验减少。她认为人们试图在生活中寻找额外的意义,谈论公共事务会让人获得关注,但容易陷入表演姿态。
苗炜:他认为每个人的道德感不同,在处理社会事件时会有不同的选择。2003年非典期间,他出于本能去医院拍摄,并没有预设目标。2003年非典期间,三联生活周刊是他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他认为2003年非典期间,多家媒体互相竞争,促进了新闻报道的突破,媒体之间的竞争可以推动新闻报道的边界。他认为媒体具有天然的不道德性,重大事件会提高销量,重大事件发生时,三联生活周刊的深度报道使其成为必读刊物。他认为每个人的道德感不同,难以拿捏报道的尺度,媒体人面临道德困境,报道事件后可能会有更好的职业发展。他认为作家和媒体人的道德感不同,对事件的看法也不同,作家和媒体人的关注点不同,作家更关注个体和细节。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当媒体人,更适合当作家或编辑,并认为自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被模式束缚。他认为减少感动和客气是一种审美需求,作家和媒体人的立场不同,对事件的看法也不同。他认为媒体具有工具性,需要满足读者的需求;作家则没有这种义务。他认为艺术家天然就有立场,需要寻找自我,作家和画家的工作模式是以不变应万变,而设计师则需要跟随客户需求变化。他认为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自己是一种消极的思路,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于个人问题,会让人越来越憋屈。他认为人们通过喝酒、夜生活等方式来逃避现实的不满,需要更多交流和聊天,避免孤独。他建议每年结识50个新朋友,减少孤独感很重要,家庭对于个人生态很重要。他认为需要重建亲密感,并感受朋友的笃定和认真,他希望身边有更多认真思考和生活的朋友。他认识的做电影的朋友这两年境况很惨。
朱砂:略
Deep Dive
访谈嘉宾们分享了疫情期间的创作状态、生活变化和心理调适。他们谈到了疫情对写作节奏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信息过载和社会动荡带来的焦虑。
- 疫情期间保持在家写作的节奏
- 信息过载和社会动荡带来的焦虑
- 疫情对写作的正面影响
Shownotes Transcript
房方 朱砂 苗炜2022.04.05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