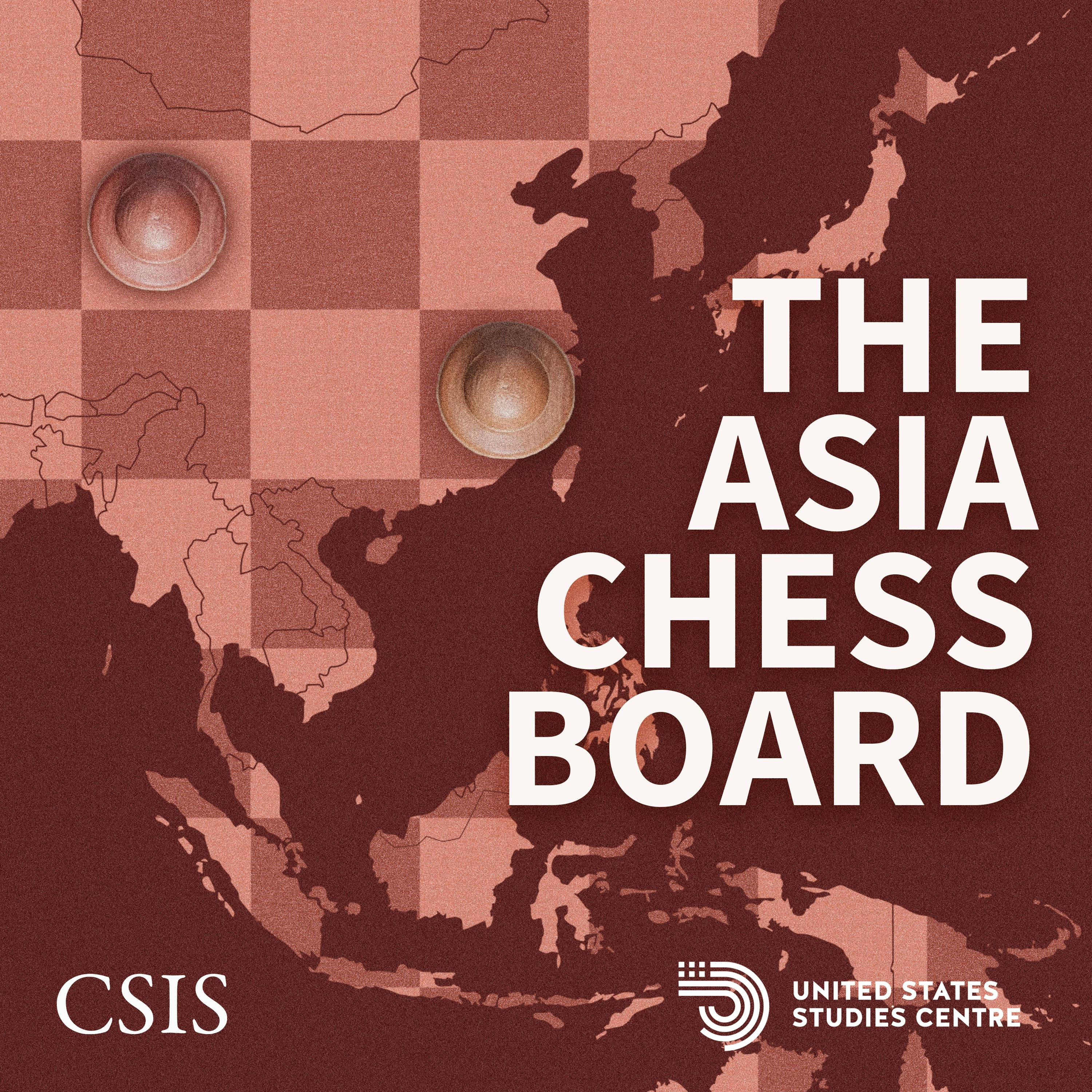
Deep Dive
Shownotes Transcript
本周,迈克和朱德邀请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美国外交政策亨利·基辛格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和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他们讨论了他们新书《迷失的十年:美国转向亚洲和中国力量的崛起》(2024年6月,牛津大学出版社)。</context> <raw_text>0 欢迎收听《亚洲棋盘》播客,该播客探讨亚洲的地缘政治动态,并深入了解大战略的制定过程。我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安德鲁·施瓦茨。
欢迎收听《亚洲棋盘》。我是朱德·布兰切特,与我的同事兼朋友迈克·格林一起。我们很高兴能邀请到两位美国最优秀、最受尊敬的战略思想家鲍勃·布莱克威尔和理查德·方丹,与我们一起讨论他们非常重要的新书《迷失的十年:美国转向亚洲和中国力量的崛起》。
我认为我们的两位嘉宾都为我们的听众所熟知。他们的个人简介太长,无法在此完整介绍,但简而言之,鲍勃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美国外交政策亨利·基辛格高级研究员。在此之前,他曾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战略规划副顾问,担任总统伊拉克特使,并于2001年至2003年担任印度大使。理查德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首席执行官。
CNAS,或者CNAS,取决于情况。智库界一直在就哪个名称更合适进行辩论。在加入CNAS之前,他是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对外政策顾问,曾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工作过。鲍勃,理查德,非常感谢你们加入播客。感谢你们的邀请。
谢谢你们的邀请。我们向所有嘉宾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关于个人经历和起源故事的。你们两位,我们都可以分别做一个关于起源故事的播客,以及你们是如何关注大战略和亚洲的。所以也许可以请你们简要介绍一下。鲍勃,也许我先从你开始。你是如何开始对美国外交政策、大战略以及对亚洲的强烈兴趣产生兴趣的?
我第一次从堪萨斯州的农场出国,当时我们认为科罗拉多州是一个遥远的外国,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去了非洲。
我回来后,令我惊讶的是,我想其他人也一样,我竟然通过了外交事务考试,成为了一名外交官。我在非洲工作过,因为我的和平队经历,我在到达那里时会说几种非洲语言。然后在伦敦,然后在特拉维夫。
所以我当然读过《纽约时报》关于亚洲的报道,但根本没有关注它。这直到,正如你刚才提到的,我去印度,小布什总统派我担任印度大使。当然,这是一个职位,
所有亚洲国家,尤其是在印度摆脱社会主义过去并伸出援手的那段时间,对美国大使来说都很重要,试图了解印度在亚洲背景下为何以及如何采取这种行为。所以这就是我开始的地方。然后我回到伊拉克战争,
然后离开了政府,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开始写作,特别是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文章。这是我关于本质主义的第二本书,其核心是中国。
第一本是关于地缘经济学和中国利用经济胁迫实现地缘政治目的的。谢谢。我还想说,鲍勃,我认为那本关于地缘经济学的书超前了。那是我读到的第一批真正关注这一点的书之一,并且我要赞扬你看到了经济策略的重要性。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了,但那本书我认为是进入现代经济策略时代的第一批著作之一。理查德,轮到你了。
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长大。我一直对外交政策感兴趣,但我的家乡并没有太多外交政策。
我一直对亚洲,特别是对日本感兴趣。所以我花了一年时间在牛津大学,并加入了日本协会,这对于我大多数同学来说并不直观。然后大学毕业后,新奥尔良有一个日本领事馆,他们在宣传JET项目,即日本交流与教学项目,我相信迈克·格林也参加过。
我从未去过亚洲,也不会说“你好”,但还是去了那里,在一所日本高中教英语。
之后,我花几个月的时间在华南、蒙古和东南亚等地背包旅行。到那时,我已经完全迷恋上了整个地区。从那以后,它就一直是我关注的地区。理查德和鲍勃,首先,我想祝贺你们出版了这本非常重要的新书,正如我多次对你们两位提到的那样,
这本书显然会成为一本
那些对大战略、对华政策和印太战略感兴趣的人在未来10、15、20年里都会阅读、争论和引用这本书。在我读的前几页,我就很明显地看出这本书是那种级别的。所以首先,祝贺你们。这也引出了我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本书的起源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本显而易见的书,但没有人写过它。当你看到它时,
也很令人惊讶的是,一本近现代史的书已经出版,并提出了如此有力的论点。所以我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嗯,它最初起源于外交关系委员会关于“转向”主题的一个研究小组。我们进行了八次会议,迈克领导了这项工作。大约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理查德和我意识到,我们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特别报告分配的8000字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决定写一本书。但在这里我要说,当然,这本书……
明确地指出,正如“转向”在公布时所设计和描述的那样,并没有发生“转向”。但我们开始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希望这是精确的。迈克·布隆伯格的慈善机构有一个座右铭,那就是“我们相信上帝,其他人带来数据”。
我们为这个项目带来了1000个脚注的数据。这就是它的发展过程。从开始到结束,我们可能花了大约两年时间才达到现在的水平。为了确定一个基线,我想问一下你们关于我们可以以此为参照的相反例子,即……
一个积极主动的、根本性的、大战略的转变已经发生,资源被重新分配,优先用于应对具体的挑战或一系列挑战。我很难想到一个理想类型的大战略转向。我们可以想到一些被动的、混乱的例子,比如全球反恐战争、冷战的早期起源,这些都发生在1945年大裂变之后。那么,你们能举出一些可以以此为参照并进行基准测试的例子吗?
说这是一个失败,你们在书中也谈到了这一点,这仅仅是民主国家的混乱现实吗?也就是说,我们在危机发生后反应迅速,但当一个问题正在出现,并且人们仍在争论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时,积极主动的转变本身就非常、非常困难。
是的,我会说这很大程度上是民主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但这不仅仅是如此。政策制定者应该能够看到并预料到重大转变的必要性,即使在没有一些灾难性事件的情况下也开始进行这些转变。你说的对,大多数这些重大转变都是灾难性事件之后发生的。有
至少可以说有一个或两个例外。我的意思是,美国和英国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在1941年就阐述了《大西洋宪章》,开始规划战后的世界,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等。当然,欧洲确实发生了危机,但我们还没有经历珍珠港带给我们的灾难性事件。但是的,这很难。很难有预见性
在很多方面,“转向”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在书中的一句话里,我们说,在某种程度上,“转向”超前了,因为它预料到了吸收与亚洲接触的好处以及应对尚未完全进入政策制定者群体的新兴中国所必需的东西。
所以回到奥巴马政府的早期,你们认为,要让像“转向”这样的战略奏效,必须明确阐明你的案例理论。而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案例理论。事实上,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奥巴马政府对
中国的性质、国际关系本身的性质存在严重分歧。你有一些自由理想主义者,你有一些像希拉里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转向”的起源,以及这些关于中国和世界观的不同观点是如何损害它的。另外,我很好奇,你们在书中没有详细谈论这一点,但……你们都曾在政治竞选中工作过,就像我一样。坦白说,奥巴马竞选活动是如何搞砸了他们的战略逻辑的?他们有多少是在自我陶醉?
那么,在2009年、2010年和2011年,是什么样的智力激荡或缺乏智力激荡,损害了或……
损害了阐明“转向”是什么的能力?因为你们正确地指出,这是个大问题。没有人清楚地阐明重点是什么。嗯,“转向”的起源可能是三方面的。在最高层,是巴拉克·奥巴马出于明显的自传原因对亚洲感兴趣。
希拉里·克林顿也在她自己的层面上对亚洲感兴趣,尽管当然,国务卿必须担心全球问题。所以我们的老朋友库尔特·坎贝尔,他是一位杰出的政策企业家,首先开始思考,然后主张这个概念。
即美国应该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将亚洲置于其议程的首位,而不是以牺牲其他重要国家利益为代价,但它显然是第一位的。
他撰写了克林顿国务卿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5000多字的文章。这篇文章确实阐述了一个“转向”的概念,长达5000字。但重要的是,它基于她的信念,即中东战争即将结束。当然,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但第二点是,几乎没有机构间的流程来支持“转向”。我们都知道,作为政府角斗场战斗的老兵,如果没有这个,要么人们事后反对它,要么每个人对它的定义都不同。当我们进行采访时,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
对“转向”的定义。而那些尽职尽责地致力于亚洲事务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我们的朋友,都是好人,聪明而尽职尽责,他们继续做他们的工作。我们从未在书中争论说对亚洲的外交停止了。
当然没有。但没有发生的是,从中东、欧洲和美国本土重新分配资源。随着十年的发展,我们在中国日益对美国重要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言辞上有所改善。但我们的行动并没有始终与我们的言辞相符,直到2010年代。
理查德,说“转向”有政治目的,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发表的“转向”和“再平衡”声明,是不是太愤世嫉俗了,或者只是有点愤世嫉俗?也就是说,是为了掩盖许多人真正想做的事情,那就是退出中东。换句话说,它从来就不是关于亚洲的,而是关于试图让美国摆脱中东的。或者这太愤世嫉俗了吗?
太愤世嫉俗了,迈克·格林。我认为这可能太愤世嫉俗了,因为据我回忆,你可能也记得,鉴于我们在2008年特别失败的总统竞选中的服务,巴拉克·奥巴马竞选时说他会从伊拉克撤出所有军队,他会每个月撤回一到两个旅,直到他们全部撤走。这与
亚洲无关,尽管当时甚至有人反驳说,我们将资源转移到中东的沙地上,错失了巨大的机会。然后,当然,在他上任之初,试图在阿富汗增兵,目的是成功结束这场战争。
所以,奥巴马总统想结束被许多政府官员视为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在中东却收效甚微,有多种理由。而亚洲则更有希望。
那是你参与拉尔夫·纳德竞选的时候吗?是的,我们让他获得了1%的支持率。太棒了。在约翰·麦凯恩的竞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鲍勃,如果你能发明一台时光机,并把自己重新塑造成新上任的巴拉克·奥巴马竞选活动的民主党顾问,
你会如何开展制定“转向”战略的流程?它是临时制定的。它是由国务卿在一篇文章中阐述的,并没有与政府的其他部门协调。正如你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是在公告之后才召开的。但如果你能发明一个更好的流程,它会是什么样子?就像艾森豪威尔的“阳光室”演习,或者应该从中学到一些经验教训。你说的对,直觉显然是正确的。
直觉是正确的。能量是正确的。库尔特尤其应该得到巨大的赞扬。但这个过程,每个人都承认,没有达到要求。那么你会怎么做?嗯,也许我可以依赖一点历史。我曾为亨利·基辛格工作。1973年,在美国过度关注越南之后……
他决定,美国必须再次将欧洲和我们的盟友作为主要关注点。他在1973年发表了一篇演讲,正如亨利总是写到最后一样。所以我当时是级别最低的人。我们听到,温斯顿·洛德和我听到他说,所以明年,
明年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欧洲年”。所以他完成了演讲,走了下来。这不是杜撰的。温妮说,亨利,欧洲年的要素是什么?他说,轮到你了。
所以这非常符合我们正在讨论的精神。而“欧洲年”经历了非常艰难的一年。我不会详细介绍它。当然,73年发生了战争等等。但这基本上是失败的。对于听众来说,更广泛的教训是,如果主动性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在各机构之间进行整合等等。它们什么时候真正有效过?那么,应该怎么做呢?你刚才说过,迈克,你必须诚实。如果有一个机构间的流程,可能永远不会有“转向”,因为政府内部对此存在如此多的争议。但把这放在一边,有什么不同吗?嗯,总统,
当时以及他的继任者从未以任何领导方式认同这一概念。
所以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是,总统,就像小布什对反恐战争所做的那样,必须站出来说服美国人民相信为什么“转向”正在发生的原因。第二,没有与盟友进行协商,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尝试和真实的格言。所以华盛顿的大使们说,
当外交政策文章发表时,他们感到震惊。他们跑去找他们最喜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务院工作人员,说,如果亚洲是第一位的,那么第二位是谁?成为第二位意味着什么?第三位是谁?而没有答案。
所以第二,他们会与盟友交谈,让欧洲人放心,告诉那些越来越确信美国要回家的中东人,我们不会回家。我们试图在书中证明我们没有这样做,但他们认为我们做了。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处于两难境地。我们没有转向,但欧洲人和中东人认为我们转向了。
而那些精明的欧洲人意识到,这根本没有发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肯定没有发生“转向”的国家是中国,因为他们有400个研究所,只跟踪迈克·格林在办公室系鞋带的时间。
所以这是两难的局面。我以哈罗德·布朗关于苏联的一句话结尾。他曾说过一句名言:“当我们建设时,他们建设;当我们不建设时,他们建设。”所以中国人知道没有“转向”,知道没有军事建设,就假装有。
并部分以此为理由证明了他们惊人的军事建设。理查德,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像“转向”这样有争议的事情,因为它当时是,现在是显而易见的,是否可以通过机构间的流程或与盟友的协商来实现,因为你知道欧洲盟友、中东盟友会强烈反对它,并将其泄露给《纽约时报》。然而,在你们的书中,你们描述了日本战略的影响力,尤其是在
为“转向”的演变增加了一些真正的纪律。澳大利亚、韩国稍晚一些,但现在欧洲和北约也在转向。所以理查德,请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盟友和伙伴的结论。没有他们,这个战略行不通。很难想象一个从一开始就完全包容的流程。你在盟友那里待了很长时间。你从整个“迷失的十年”的经历中得到了什么启示?嗯,日本在其对亚洲安全和经济动态的理解以及它自身在这一切中的作用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转变
过程。所以人们可能会记得,如果你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例,它不仅被广泛认为是“转向”的经济核心,而且在美国退出之后,在
与日本讨论了其巨大优点并帮助日本加入之后,东京自己带头完成了这项工作。在智力层面,是日本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概念,后来当然被美国自己所采用。迈克,正如你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如果你谈论过
日本走在美国前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走在美国前面,它正在弄清楚自己的目标和对华政策。美国非常擅长识别我们不想在中国看到的景象。我们不希望中国主导南海。我们不希望他们入侵台湾。我们不希望他们压迫维吾尔族人。我们不想这样做。我们不想那样做。
我认为,迈克,你已经阐述了日本的一种总体方法,那就是他们希望免受中国的安全威胁,并希望在中国贸易和投资市场上发财。这是否能够实现,也许是一个单独的问题。澳大利亚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澳大利亚在私下和公开谈论印太地区军事力量平衡恶化的问题上,
比华盛顿普遍谈论这个问题早了好几年。他们在国防白皮书中写下了这些内容。他们确实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军队的未来将不会是,你知道的,与美国一起前往阿富汗的山区,而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第一次更靠近他们自己的邻里,考虑到中国的崛起。所以
盟友不仅扮演着盟友的关键角色,而且他们还扮演着“矿井里的金丝雀”的角色,比华盛顿达成共识更早地感知到该地区不断变化的动态。澳大利亚现在是冬天,我的声音也哑了。所以我再补充一点。把它交给朱德。
来总结一下。顺便说一句,这是一本很棒的书,在我完成之前,我非常喜欢阅读它的不同版本。“一千个脚注”绝非夸大其词。这不仅仅是偶然的。有很多数据。所以我们谈论的关于“转向”的争议是关于远离欧洲或远离中东的争议。但还存在另一种紧张关系,那就是……
转向亚洲的什么?你们还有另一个有争议的想法,奥巴马总统也没有亲自对此发表意见,那就是新的超级大国关系模式,即与中国建立双极共管的想法。有多少战略实际上是关于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辩论,或者我们将进行什么样的转向?因为许多奥巴马政府官员会说我们确实转向了。我们对中国进行了战略安抚。我们进行了战略和经济对话。我认为到最后是这样。所以有多少实际上是关于什么的争议
这将确保美国的亚洲利益。如果你查看奥巴马政府的文件,除了我们对主要官员的采访之外,你会发现一个接一个的文件说,一个文件说“转向”有五个支柱。下一个说“转向”有三个支柱。下一个说有六个半等等。
就像蒙提·派森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一样。是的,完全正确。所以我将这样总结,我很想知道理查德,事实上是你们两位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将这样总结。当“转向”被宣布时,许多人仍然抱有一种希望,我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仍然抱有一种希望,那就是
中国可以被诱导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人们错误地批评鲍勃·佐利克,因为他当然没有这么说。他说,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他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没有保证。
所以这种希望体现在一种粗略的共识中,这将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我们将对这种可能性不发生或没有发生的情况进行对冲。
问题是,随着2010年代的推移,直到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表达,我们一直抱有希望,希望能够实现一种更融洽的转变,而数据却越来越糟糕。对冲从未与伸出援手相匹配,试图将他们带入我们对世界秩序转变的概念。
史蒂夫·哈德利公开表示,他们误判了习近平。我曾经对他说,我认为你过于自责了。
因为我认为在他上任时,并没有大量的分析人士预见到他会把中国带向何方。但我们确实很慢才意识到他将中国带向何方。所以她的演讲,我希望这会在书中体现出来,理查德也从这一点开始,她的演讲既关乎亚洲的希望,
也关乎处理中国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它更多的是关于亚洲的希望,因为那些官员没有意识到中国将走向何方。理查德,鲍勃预料到了,事实上,推翻了我接下来关于史蒂夫·哈德利对自己误读习近平而自我鞭挞的大部分问题。
我会发表评论,然后提问。评论是,我认为如果鲍勃只是说,我认为我们有时对“错失习近平”过于批判。我当时住在中国。我大多数被归类为精英的中国朋友最终都误读了习近平。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的许多政治制度都误读了习近平,因为如果他们知道
他将成为一个多么野心勃勃的领导人,他偏爱清洗解放军和安全部门,他们就不会同意他的崛起。但我确实想问这个问题,习近平的特殊领导人和领导风格在“迷失的十年”以及更重要的是未来战略中的地位如何?这是反事实的吗?你认为我们应该走同样的轨迹吗?
如果领导人不是习近平,而是一个“胡锦涛2.0”类型的领导人。换句话说,在你回顾过去十年时,这是制度问题还是个人问题?
我认为习近平加剧了,并使该制度先前产生的一些事情变得更加坚定或具有侵略性,如果还有其他人,它也会产生这些事情。所以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问题。嗯,习近平并没有建立军事力量。
我的意思是,建造了一些军事设施,但并没有建造军队。我的意思是,这可以追溯到胡锦涛、江泽民以及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中国领导人和解放军发生的军事投资等等。所以即使你换了一个领导人,你也会拥有更强大的中国军队。
它的经济引力可能与领导人无关,无论如何都可能处于类似的轨迹上,你知道的,如果没有习近平压制他自己的经济,特别是科技经济,它实际上可能会有更大的经济引力。但这是力量的使用。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做了两件事。第一,
推翻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是一个近期现实目标的任何概念,因为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不仅没有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而且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它正在为地区和全球秩序提供替代方案,试图推翻它不喜欢的地方。然后,当然,在国内,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通过贸易和信息流以及中产阶级的增长以及与中国的深度接触,你会看到中国的国内自由化,甚至有一天中国的民主化。当然,在习近平领导下,这也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所以它更具有压迫性……
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国内比在胡锦涛和江泽民领导下更具有压迫性。所以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华盛顿和东京这样的首都,我认为习近平及其行动在帮助形成已经出现的共识方面几乎是决定性的,即与中国接触的旧方式以及我们以前所希望的事情,如果它们曾经存在的话,现在已经不再现实了。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听听你们两位对此的看法,这是关于你们在书末尾提出的前瞻性战略的交叉点,我认为其中许多建议都得到了华盛顿特区外交政策机构的全力支持,但似乎与我们看到的美国国内政治走向相悖。重新加入CPTPP,我认为你会得到90%的支持率
当然,在CNAS、CFR和CSIS所在的七个街区内是这样,但如果你走得更远,支持率可能会下降。真正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因此,将这种建议的战略转变
与你在未来10年看到的国内政治现实联系起来,无论是在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还是2028年的政府,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我想说,尤其是在贸易政策方面,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是,每位总统都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这
至少在更广泛的政治层面上,将使贸易协定成为可能,无论是CPTPP还是像数字贸易协定这样的垫脚石,无论是双边、区域还是部门贸易协定。现在,你仍然需要一位想要这么做的总统。但如果你从历史上看,总统在第二任期比第一任期更有自由去追求这类事情。
当然,2016年是转折点,像TPP这样的东西在2015年一年之前就被证明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贸易促进授权通过了国会。所以,是的,从那时起,很多政治上的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这些事情确实会起起伏伏。我认为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一些在政治上曾经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为可能了。
就在几年前,你不可能想象出5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用于半导体产业。但人们认为这对于有效地与中国竞争是必要的,这使得它在政治上变得现实。再往前几年,你不可能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支持的《建设法案》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但现在你可以了,因为人们相信这是必要的,才能在政治上
应对中国的挑战。因此,即使这些事情中的一些国内政治并不完全受欢迎。这使我们能够做一些以前不可能的事情,但它还没有让我们去做最难的事情。
最难的事情包括贸易政策。这将包括一项战略性移民政策,让最优秀、最聪明的工人留在美国,为创新经济做出贡献,这样他们就不会去中国或其他国家。这将包括对我们的部队结构、我们购买的东西、我们如何购买它们以及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重大改变。到目前为止,除了最后一点,当国会现在似乎正在积极行动时,
这是不可能的。但模式是,随着对中国挑战的日益增长的敏感性持续增加,这使得打破一些国内反对意见成为可能。所以,我想,拭目以待吧。
好吧,每个人都有理由说这有多难。我们的一位朋友,我不会说是谁,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人说,哦,这些都是很棒的建议,而且都是痴人说梦。我说,好吧,那还有什么呢?
但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发言,他的独白。我只想说两件事,因为我认为理查德已经很好地举例说明了,几年前似乎是痴人说梦的事情。作为我们迄今为止复兴的架构师和主要管理者,习近平正在帮助我们更接近于做一些这些事情。
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我们国家有多认真的一次考验。
我们知道我们持续远离我们在亚洲和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影响,权力平衡向中国倾斜的各个方面。我们知道中国的目标,那就是取代我们成为亚洲及其他地区最重要的国家。所以我们知道挑战是什么。
但我们会做到吗?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认真到足以做到吗?我最近看到一个丘吉尔的定理。他说,美国对深远的外国危险的反应总是很慢,但从不慢到无法反应。
好吧,让我们看看这次我们是否太慢了,最终,这不会超过十年,
如果我们没有充分应对中国,它将开始改变普通美国公民生活的性质。理查德,鲍勃,很好的结束语。理查德,乐观的一点是,曾经在政治上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有领导力的勇气,再加上习近平过分出牌,就能成为可能。鲍勃,为领导力、政治领导力抛出了挑战。
为了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而付出必要的政治资本来进行这些改变。所以,再次祝贺你们两位。一本书,同意它,不同意它,每个人都必须努力阅读、讨论和争论,才能在这个领域认真对待,我认为这是所有在亚洲政策方面写书的人都渴望达到的目标。所以你们已经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祝贺你们两位。感谢你们两位在上周就做了400次读书会演讲。
谢谢,朱德。谢谢你,迈克。谢谢。感谢你们的邀请。更多关于战略和亚洲项目的工作,请访问CSIS网站csis.org,然后点击亚洲项目页面。更多关于悉尼美国研究中心的信息,请访问ussc.edu.au。